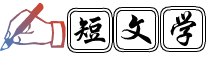罗锅大叔是我爷爷的外甥,也就是我爸爸的表哥,我小时候经常听奶奶讲罗锅大叔的事,由于他家离我村不远,所以我对他的事还是了解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罗锅大叔的事越来越清楚。
罗锅大叔一生下来就是罗锅,不过他在他家是长子,父母痛爱有加,他哇哇坠地,父母一看是男孩,心内高兴,也就没有注意他身体的畸形,因为在农村男孩是个宝。到了5、6岁的时候,罗锅渐渐明显,加之40年代的医学也不发达,家人也没有在意。倒了20岁左右,也就是60年代正值全国闹饥荒,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给他治病?眼看着他年龄一年年长大,到了该结婚娶媳妇了,可一个罗锅背在身上,家里又穷,村里和他一般大的同龄人的孩子都在地上跑了,可他还是孤身一人。
由于身体原因,也干不了什么重活,村里就照顾他让他给生产队放羊,于是他天天赶上羊群早出晚归,成了一个没人理、没人问的放羊娃。
到了30岁那年的一个秋天的早上,天刚麻麻亮,罗锅大叔就赶着羊群出门了,到了快出太阳的时候却不见太阳的影子,四周被浓浓的大雾包围着,这样的天气对罗锅大伯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农村放羊娃哪能不遇上几个雾天?就是刮大风,下暴雨也是常有的。他像往常一样把羊赶到山上看着羊儿吃草。自己却放开喉咙唱起了陕北信天游:
六月里黄瓜下了架,
空口口说下些哄人话。
一对对山鸡隔沟沟飞,
一个庄庄相好还没机会。
一对对鸭子一对对鹅,
干妹子在捡畔上照哥哥。
我和哥哥有说不完的话,
咱二人死活常在一达达。
一山山高来一山山低,
掏一回苦菜我看一回你。
你给我说你给我笑,
道不如给我唱曲解心焦。
满肚子心事没法说,
单给你送一颗红果果。
牵牛花开花在夜里,
哥哥我有个小秘密。
日头头升起来照大地,
看得清我也看得请你。
山丹丹开花羞红了脸,
哥哥你让我咋跟你言?
司马光砸缸就一下,
豁出去告诉你我心里话。
黑夜里月牙牙藏起来,
扑通通钻进了哥哥的怀。
云从了风儿影随了身,
哥哥妹妹从此不离分。
圪梁梁光光任你走,
一夜里三次你吃不够。
村东的河水哗哗地响,
妹妹我快活的直喊娘。
花瓣瓣落下果子熟,
要生个娃娃满地走。
树叶叶落下只剩了干,
哥走了我夜里长无眠。
烧开的水后有下锅的米,
马配上了鞍后没了人骑。
晴天里打雷真真个怕,
哥哥你在山上想起了她。
一阵阵狂风一阵阵沙,
妹妹的心里如刀扎。
黄河水它流走回不去,
几回回哭得我快断了气。
大雁雁南飞秋声声凄,
慌了责任田你富了自留地,
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0,
这么好的地方留就不住你。
……
他声音拉得老长,粗狂的就像一只失了群的孤单单的狼一样嚎着,声音穿过浓雾、越过高山、钻进茂密的丛林,震落了叶儿渐渐发黄的小草上边的露水,惊飞了藏在密林中的两只山鸡。他唱着唱着一汪泪水盈出眼眶,也不擦,面对着浓浓大雾,任由泪水纵横,感到心内非常孤单,虽然身体残疾,可他毕竟还是一个智力健全的男人。30岁的人了,还孜然一身,在这荒山野岭,大雾弥漫只能看见自己的天气,他放开了思想的野马,任由思绪驰骋,想这人活到世上,就是一个贱,就像这漫山遍野的荒草一样,本来生的就低贱,任由人类践踏,畜生糟蹋、或者干旱、或者寒冷,要不就来上一场火灾,但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却还要挣扎地活着,究竟图啥呢?正想着,却见不远处的大路边有一团黑呼呼的东西,他也没有在意,以为是谁丢下的烂衣服什么的。正准备坐下歇一歇,却听见有人在说话,仔细再听,分明是有人在喊叫什么,怪了,这样的鬼天气,在这荒山野岭,能有人的声音?他顺着声音往前走了两步却见那团黑东西在动,他下意识的握紧了手里的放羊鞭子,大着胆子往前再走了几步,又听到一声:
“……饿”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挺好听的,脆脆的、嫩嫩的。
30岁的单身罗锅大叔在这样的天气里听到这样的声音心内先是一惊,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朝四周看看,没有人呀,他擦擦眼睛再仔细看,周围还是大雾一片。
“大哥,俺饿”
这一次他听清了,那团黑东西原来是一个人,是一个不知从啥地方冒出来的女人,那声音怪怪的,他有点听不懂。仗着手里的放羊鞭子,他又向前靠了靠,这下看清了,那女人穿了一身分不清颜色的灰不拉几的衣服,头发有点乱、也有点脏,不知道上边沾了一些是草还是什么东西,脸和手都很脏,看起来有几天没有洗了,她卷缩成一团,身旁放着一根曲里拐弯的木棍,木棍的一头磨的没有了皮,很光滑。也许是冻的吧身子发抖,一双无神的眼睛死死盯着罗锅大叔看。
罗锅大叔被这突然出现的、不知来历的女人吓傻了,死死盯着她的眼睛足足有一分钟。
“你是谁?怎么坐到这儿?”他揉揉眼睛终于鼓足勇气问道。
“俺饿,大哥,救救俺,俺是逃难的”
“逃难的?你……你家是哪打的?”
“河河......河南,大哥,俺…………俺饿,给点吃……吃的吧”
“吃的?……”
奥,原来是个要饭的,她身子发抖,是饿的或许是冻的,也不知罗锅大叔此时出于什么心内,他毫不犹豫的脱下自己身上的夹袄披在她身上。
“吃的……,你,你等着!”
平时走路木南罗锅大叔此刻非常麻利的跳下马路到马路下边的也不知是谁家的地里快速的拔了俩颗红萝卜,拧下萝卜叶快速地擦了擦,扔掉萝卜叶,又一边往上跑一边用手把那俩个红萝卜擦净,气喘吁吁地跑到那女人跟前赶快递给她。也许是太饿了吧,那女人接过红萝卜,就狼吞虎咽的啃了起来。
“慢慢吃,慢慢吃,你说你是逃难的?”
也不管他的问话,那女人只顾低头啃萝卜。
“你说你是逃难的?”
……
终于,那女人啃完了俩颗红萝卜,身子动了一动,企图想站起来。
“你说你是逃难的?你是哪里人?”罗锅大叔又问。
“俺家是河南的,家里遭水灾,家人都没了,俺是要饭来的,大哥,俺饿”
“饿?还饿?”
看着眼前这个要饭吃的女人,他心想,那么大俩萝卜还不够,看来好几天没吃东西了,看看周围仍然是大雾一片
“你等着”
罗锅大叔朝四下里望了望,很麻利地钻进附近的包谷地里,抖落了包谷杆上的露水,拜了俩穗包谷穗猫着腰出来了,也不顾腿上的泥,脸被包谷叶划了几道红红的印,他觉不到痛。就地取材急急地拾了几支干树枝打了一堆火,等到树枝烧完后,他把那包谷穗埋到火灰里,一会功夫,他用柴棒划拉出来,抖掉上边火灰,顿时一股浓浓的香味直扑鼻孔,那女人睁大眼睛看着罗锅大叔忙活,也在不知什么时候蹭到火堆旁,接过那热乎乎的包谷穗又急急地啃了起来,直啃得脸上沾满了黑黑的包谷渣子。一穗吃完了,把另一穗踹进了怀里。罗锅大叔看她吃完了,又递上随身带的水壶:
“你打算到哪去?”
“……”那女人摇摇头
“那你晚上住哪儿?”
“……”
也许是刚吃完东西,加之在火堆旁烤了一阵火,那女人脸上有了红润,虽然看不出她的年龄,但毕竟是个女人,罗锅大叔心内某根神经动了一下:
“要不,你下午跟我走,到我家,你晚上和我妈住一屋。我们这地儿也穷,不过,多一半个人也无所谓”他以极低的声音试探着说。
“大哥,你家远吗?”
“不远,不远”罗锅大叔急急地回答。
……
就这样,这个逃难的女人被领回到了罗锅大叔家里,父母自然高兴,罗锅妈给烧了一锅热水让她好好洗了一个澡,又找出自己的几件净衣裳让换上,梳好头发,全家人惊呆了,没想到,她竟然是个大美女:1.70m的个子、长头发、皮肤雪白光亮、一双忽闪着精灵的大眼睛含满了水、细长眉毛双眼皮、樱桃小口厚嘴唇、嘴角一边有一个小酒窝、下巴圆圆的、胸脯挺挺的、腰儿细细的、屁股翘翘的,整个人清清丽丽,给人一个鲜亮而有福气的感觉,她站在屋里,仿佛整个屋子都亮堂了许多。
罗锅妈围着这个女人转了几圈,嘴内砸把着“吱吱,这么好看的女娃出来要饭,有好脸蛋没有好命,唉!也难怪,这世道有几个人好过的?”她又想起了罗锅,30岁了还是孤身一人,想着想着,罗锅妈笑了。
……
经过村里人的作合,这个逃难的女人做了罗锅的老婆,那时她才24岁。村里人背地里都说可惜了这女娃。从此后,罗锅大叔结束了他的单身生活,人也精神了不少,仿佛那背了罗锅的腰杆也挺起了许多。
到了第二年冬天,这女人罗锅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孩子刚出生,剪断脐胎后,罗锅妈担心身体有毛病,把孩子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几个遍,欣喜的发现,没有毛病,于是给他取名“端正”。
儿子的出生是罗锅大叔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终于堂堂正正做了爸爸,和别人一样了,因为在陕西的农村,尤其在野鸡岭这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小山村,男人在30岁以前不结婚会被人议论有毛病,结婚后该有孩子的时候而没有,会被人乱猜疑。忧的是本来生活就过得艰难,尤其没有吃的,而今又添一张嘴。所以,在儿子出生的第三天,罗锅大叔向邻居借了20元钱,他先到商店买了一串500头的鞭炮,给老婆买了2斤红糖,到邻村买了一篮子鸡蛋。回家后先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了一个装满面土当做香炉的碗,在内边恭敬地插上三柱香点着,对着初升的太阳,燃放了那500头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引来了一群吊着鼻涕的小孩,争着抢拾地上那没有放响的零鞭。罗锅大叔很虔诚的跪倒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嘴内念念有词:“菩萨爷保佑我儿全全换换,平安神保佑我媳妇健康,保佑我全家好好的!”
做完这一切,罗锅大叔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他爬起身又急急地跑到铁匠部买了一把头、一把镰刀。又在路上顺便砍了两根把、两根镰把。从第二天开始,罗锅大叔每天早上把羊赶到山上让羊吃草,他自己开荒挖地。打从老婆怀孕时他就瞄准了他放羊的山上有几大块荒地能开挖,只是迟迟未动手。因为在70年代农村土地政策还不是很开放,有的村责任到户,有的还是大集体,他们野鸡岭村也在吵吵着要分地,可吵吵归吵吵,一直还是大集体。谁也吃不准政策会怎么变,弄不好会违反政策,被村里做个娃样子,那样的话事就弄大了。儿子的降生,是罗锅大叔顾不了那么多了,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做娃样子就做吧,只要有饭吃叫干啥都行。他一边开荒一边盘算着在新开的荒地上先种上两料麦子,在麦地内栽上花椒树,首先有粮吃,几年后花椒树挂果能卖钱。抽空再到山上刹上一些楣条可以利用晚上和下雨天编上一些框子,拿到集市上去卖还能挣钱。他算着干着,每天傍晚收工时把头藏在地里,第二天出来时又担上一担羊粪。在他心内有一股用不完的劲。每天,他弓着腰、担着一担粪、吆喝着羊群、嘴里还哼着小曲,谁也听不清他就究竟唱的啥,反正是乐呵呵的,人也显得精神了。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土地全部包产到户,罗锅大叔遇上了好年成、又有好政策,他开了10亩荒地加上村内分的8亩责任田,他栽的花椒树起步早、挂椒早。生产队的羊被分完了,他自己又给自己买了一圈羊。有了吃的、钱也不缺,儿子也长大了,成了16岁的大小伙子,罗锅大叔的心内乐开了花。他干着活又唱开了:
听见干妹唱一声,浑身打颤羊领牲。
你吃烟来我点火,多会把你的心亏着。
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豆钱钱下上米,路上搂柴照一照你。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扇门单扇扇开,叫一声哥快回来。
满天星星没月亮,叫一声哥哥穿衣裳。
满天星星没月亮,小心跳在狗身上。
街当心有狗坡底里狼,哥哥小心狗闯上。
白脖子狗娃捣眼窝,不咬旁人单咬我。
半夜里来了半夜里走,哥哥你好比偷吃的狗。
太阳出来一点点红呀,
出门的人儿谁心疼。
月芽出来一点点明呀,
出门的人儿谁照应。
出门的人儿谁照(呦号)应
……
猛然,在他的荒地下边公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警笛声:
“呜呜呜”“呜呜呜”……
罗锅大叔停下手中的活侧耳细听,那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那红色的警灯在转着圈的闪,望着那远去的警车,罗锅大叔笑了,他自言自语的说:“这警察也真是的,你要去抓坏人却闪着警灯鸣着号,叫人跑跑跑、跑跑跑,呵呵,你能抓住人吗”?还有那救护车声音,病人还没上车,你就在“毕了、毕了”地咒开了,那病人死了与你有啥好处?真是的没一点人性。他干着活,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可他还不想收工,就想多干一会儿,刚下了一场好雨,出土不几天的晚包谷苗需用酥土。可是不回家又不行,天说黑就黑了,羊群也不愿再呆了,早早的都往回走了。他收拾好锄头,背了一捆楣条,到羊圈圈好羊,边往回走边想今天老婆给做了啥好吃的?
他放下楣条,正准备舀洗脸水,不料从他家冲出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按倒在地一副冰凉的手铐铐上了,又不容他分说被推上了警车,他一细看,在离他家不远的打麦场里一溜串停了七、八辆警车。他被推上警车后,警笛声再一次响起,这一次是一连串的“呜呜”声。
罗锅大叔那里经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到了哪里?他打从一上警车就被吓得尿了一裤子,车一停稳,他就被两名警察提溜了下来,推进一间房子,强行按在一把椅子上,周围站了好几名警察都端着枪,一个当官摸样的警察威严的在他对面的桌子前坐下问他:
“姓名?”
“罗锅”
“问你学名”
“程罗锅”
“年龄”
……
正问着,一名警察进来了,趴在那名问话的警察耳朵边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那警察一挥手,旁边站的一个警察上来给他打开了手铐说:“走!”就这样,罗锅大叔又被警车送回了家,这一次没有拉警笛,也没有人说一句话。
进了家门,老婆不在,他就去了他父母亲的屋里。见他回来了,父母二人没有一个说话,都吊着脸咳声叹气地。罗锅大叔感到莫名其妙,问了好几声:“究竟怎么啦?端正妈呢?”
“唉!真把人丢死啦。罗锅……”罗锅妈哭了。
原来,自从罗锅大叔领回了河南要饭的女人做了老婆以后,村子里的好多人心内不自在。由于野鸡岭村人口少、文化落后,人们的思想都还存在着小市民意识,自己没出息,却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一个背着罗锅的放羊娃,也不知道他罗锅家烧了多高的香,竟然祖坟冒青烟了,一分钱没花,凭什么就娶了这么个好媳妇?村内人,尤其是男人吃完饭没事干在一块抽烟侃大山,谷堆、满囤、还有程娃三个人在一起打扑克牌,满囤说:
“罗锅拾的媳妇脸蛋白、屁股大、双眼皮、小腰卡,我一见家具就翘起了”。
谷堆边出牌边说:“妈的,这世道不公,偏偏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你会不会说话,那叫鲜花被狗屎糊了”谷堆不服气地说。
“打牌、打牌,你的屎也去糊”程娃不高兴了呛了谷堆一句。
“哎哟、哎哟,怎么,心痛啦?又不是你老婆,你心痛啥呢?看我哪天非把她压倒不行!”谷堆看着程娃的眼睛说。
“就是,压倒也白压,叫咱也尝尝不要钱女人的滋味。我就想不来,那罗锅晚上怎么做事呢?”满囤流着哈喇子起哄道。
程娃和罗锅是邻居、又是罗锅大叔的自家兄弟,比罗锅小4岁,平时两家人来往比较密切,罗锅老婆刚来不久和村内人不熟,没事的时候就到程娃家和程娃老婆爱萍拉家常。不知为什么,罗锅老婆一来,程娃就觉得很兴奋、也很殷勤,不是给取水果就递茶水。久而久之,罗锅老婆到他家也就随便了,有时候还和程娃耍耍笑。按道理程娃应该称呼这女人为嫂子,由于程娃比罗锅小比这个女人大,两人见面谁也不把谁称呼啥,这俩人的随便,爱萍也习惯了。
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罗锅一大早就吆着羊上山了,他父母也都到地里去了,罗锅媳妇在家无聊,就到他家的菜地去锄草,他猫着腰锄着一席韭菜行子中间的野草,想起了她的家乡河南,父母、姐姐都被活活饿死,只有她一人夹杂在逃荒人中间出了河南,一路要饭才到了这个叫做野鸡岭的村子,稀里糊涂做了罗锅的老婆。虽然她心内有一万个不愿意,可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在罗锅一家对她好,那二位老人把她当亲生闺女一样,罗锅更是没得说,什么重活都不叫她干。她在家就是做做饭,干干家务。自从和罗锅结婚那一天起,每天晚上,罗锅回来不管有多累,他都抱着她亲不够,爱不够。一想起这些,她就觉脸红、发烧。有时也觉得心亏,唉!女人,谁也逃不出嫁人的命运,就认了吧。其实罗锅是个好人,可惜是个腰不展…….
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天空“轰隆隆”一阵雷声在头顶炸开,四周霎时乌云密布,她一看不好天要下雨,拉起锄头就往家跑,可是没有等她跑出地头,暴雨已经兜头而下了。当她跑进家门时浑身已经被浇成了落汤鸡一样,一看不好,出门时走得急把钥匙忘家里了,她进不了门,看看雨还没有小的迹象,她想都没想就朝隔壁爱萍家跑去。
也许她被雨淋昏了头,“咣”的一下推开程娃家的大门,不料程娃穿着一条裤头从屋里蹦了出来,一见是她,又急忙转身朝家里跑。当时她啥都没想就跟着程娃跑进了他家,程娃急忙拉了一条外裤站在地上穿上,那女人一见程娃紧张的样子“咯咯咯”的笑了起来。程娃慌忙走到电视机前就要关电视,那女人笑着说:
“关啥呢?叫俺也看一看,俺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电视”。
程娃“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红着脸说:
“这……这 ……这你不敢看”
“哎呀,看你小气的,你敢看,俺就不敢看?爱萍妹子咋不在家?”
“她到她娘家去了,后天回来。”
“那你一个人在家看这么好的电视机,罗锅都没钱买,你开开,叫俺看一下。”
程娃一边关电视机旁边的另一台机子,一边不好意思的说:“这是A片录像,女娃不敢看”